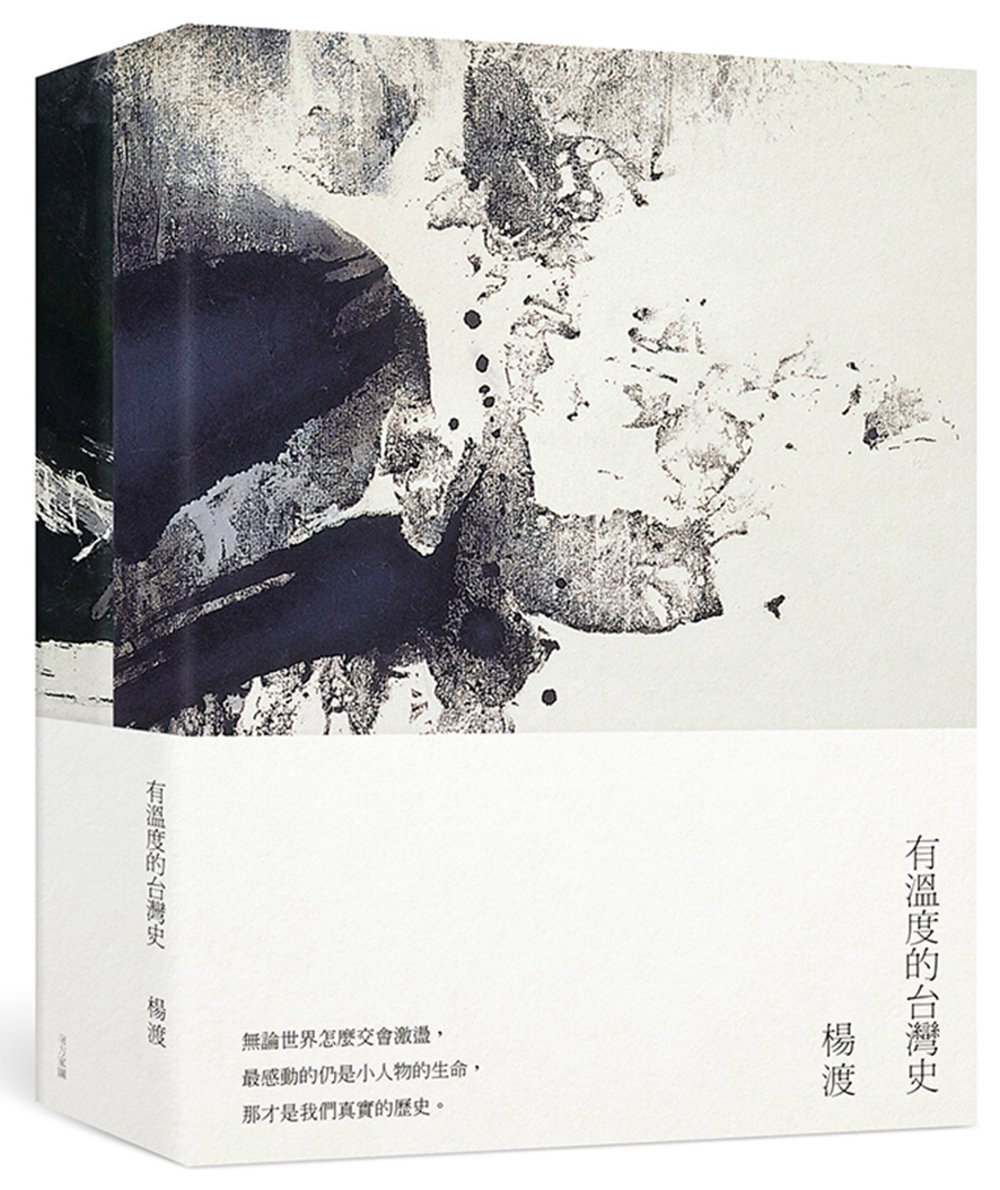
編輯人語
知名作家、資深媒體人楊渡先生之力作《有温度的台灣史》,出版經年,深受文壇推重。《優傳媒》有感於其敘事之生動,觀察之細膩,胸懷之宏闊,特選輯其所撰1945~1949年間數篇,以見初返中國之台灣人文風貌與社會變遷。撫今追昔,温故知新,應具興味而別有所悟焉。
1)驚疑還似夢──光復剎那的台灣 作者/楊渡
小學六年級的那一年,林文月在上海就讀日僑小學。1945年8月15日那一天中午,學校召集老師和學生,要一起聽「天皇玉音放送」。「玉音放送是重大的事,學校召集師生在禮堂裡,一片肅穆,安靜的聽著。天皇一個字一個字說出來的「無條件投降」的聲音,像一面大鼓,擊打著師生的心。剛開始,大家眼神茫然悲哀的相望,隨後,一聲低低的啜泣,像傳染一般,感染了每一個人。整個禮堂裡,充滿哭泣的聲音,久久無法平息。
林文月回到家中,發現並無異樣。家人慶幸著,戰爭終於結束了,台灣結束殖民國的統治。過了兩天,家人告訴她,我們現在屬於戰勝國的一方,不再是殖民地二等公民。新的時代來臨了。
然而過了幾天,上海的街道起了變化,日本人要遣送回國,但作為戰勝國的子民,台灣人沒有人管。街道上開始抓「漢奸」。舉凡穿著日式和服,或者與日本有往來的人,被視為漢奸,在路上會被抓、被打。經過五十年的殖民統治,台灣人的生活基本已經日本化,一下子要改變也很難。何況他們住在租借區,非常危險。她的母親是連雅堂的長女,連雅堂是寫《台灣通史》的文化人,他們並無政治的依靠。不得已,全家趕緊搬回台灣。那一年秋天,她回到台北開始上小學,學習中文。
林文月是一個典型。
對台灣人來說,五十年的殖民統治不是像香港,有一個租借的時限,而是無限期被割讓出去的。沒有人知道是五十年還是一百年,永久被割讓出去了。五十年後依照〈開羅宣言〉而來的「重回祖國懷抱」,竟像一場夢。人們起初都不敢相信。
8月15日那一天,陳逸松在律師事務所習慣性的打開收音機。前一天他已經聽說次日有「重大放送」(重大消息要播放),所以特地抽空聽一下。但他的收音機性能有些問題,雜音很重,聽不清楚,只隱約聽到「一心一意」「奮戰」等字眼,他心想,還不是鼓吹「聖戰」而已,於是走到隔壁的山水亭去找音樂家王井泉吃飯聊天。他很喜歡吃王井泉的「東坡刈包」。
兩人正在閒聊的當下,在「東港事件」中強逼陳逸松「無罪自首」、好讓他升官的台北州特高警部補佐佐木倉皇的跑上樓來,一臉驚惶,急切的問道:「陳先生,你對這件事有什麼感想?」
陳逸松吃過他的苦頭,怕是在套話,羅織罪名,就不痛不癢的回道:「只有照天皇陛下所宣示繼續奮戰而已。」
「唉!我聽是日本戰敗宣佈投降,怎麼會繼續作戰呢?是不是我聽錯了?請你們兩位稍候,我先回去州廳再仔細打聽,馬上就回來。」
佐佐木飛也似的衝下樓去,留下他們兩個老朋友面面相覷,王井泉的臉頰微微顫抖著,望著陳逸松說:「佐佐木不像是在開玩笑,你是不是聽錯了?日本真的投降了?」
「佐佐木說的恐怕是真的,我那破收音機根本聽不清楚。」
陳逸松記得,大約有十分鐘的光景,他們兩個人沉默不語,多少年的心事,多少年的奮鬥,多少年的夢想,竟而有這一天。
王井泉用台語輕聲說:「日本若輸去,我們所期盼的較理想的社會就會實現了。大家要好好努力呀!」
過不久,佐佐木回來了。他激動的說:「陳先生,王先生,日本輸去了。日本輸去了。太久受大家招呼,真感謝你們!」說完放聲大哭起來。他們也不知如何安慰,也不敢流露出開心的樣子。沈默中,佐佐木就邊哭邊下樓走了。
王井泉去廚房沏了一壺好茶,坐下來靜靜相對,面含微笑,慢慢品嚐。陳逸松永遠記得那個茶香,因為幾十年來,他未曾如此輕鬆過,此生第一次,放心,安心,靜心,聞到茶香。
陳逸松的作家好友,台南醫生吳新榮在那一天中午打開收音機,要聽天皇廣播,發現它沒電,就作罷了。晚上,他的好朋友跑來找他,慌慌張張的告訴他天皇播放的內容。他嚇了一大跳。但也不敢真的相信。長久的壓制,讓他保持警惕。他一直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,年輕時候坐過的牢,讓他學會不要相信統治者。
次日上午,吳新榮照常去診所出診後,才約了幾個朋友,來到郊外,把衣服都脫了,跳到溪水中,他們要「洗落十年來的戰塵,及五十年來的苦汗」。
上岸後,在空曠的天地間,在無外人的海邊,吳新榮放心對著大海高喊:「今日起,要開始我們的新生命啦!」
第二天清早,他到一個防空壕裡拿出一面祖先的神位,把日本強制擺放的「神棚」移開,齋戒沐浴後,焚香向祖先在天之靈祭拜說:日本已經投降,祖國得到最後的勝利,台灣將要光復!
雖然如此,吳新榮並不放心,台灣民眾在街道上張燈結彩,但內心還有隱憂。因為日本還有近十七萬軍人,加上日本居民,合計有五十幾萬。他們是要去要留,還未決定;如果留下,會不會發生變數?他們會不會大開殺戒?未來中國將如何接收?國際局勢會如何演變?這誰也不敢說啊!
吳新榮為了探聽消息,特地應一個日本朋友的邀約,去他的家裡探望。在日本戰敗的氣氛裡,這也是一種友善的表示。那日本朋友姓平柳,主管特務工作,因為長期監視吳新榮而有交集。他把吳新榮請到了他的防空壕裡。
在戰爭後期,美軍時常轟炸的時代,許多台灣人都躲到鄉下疏散,日本特務無法疏散,做一個大防空壕並不意外。只是吳新榮沒想到這個防空壕點著燈,不僅燈光明亮,還備有美酒和酒菜。
「日本到底戰敗了,從今天開始,我們變成戰敗國民。」平柳喪氣的說。
「但台灣人也不是贏了,怎能說是勝利國民呢?因為我們一向是順從的,在這連戰連敗的中間,也未曾和你們抵抗過。」
事實上,到了戰爭後期,軍國主義橫行,所有反抗都已被壓制,連用收音機聽大陸的廣播都可以入罪坐牢,台中中央書局的莊垂勝就是因此坐了一年的牢,嚴厲至此,誰敢反抗呢?
「是,是,這我們也知道,所以未曾放行那個最後處置。」平柳說。
「什麼最後處置?」
「這也是過去的問題了,所以我也願意說給你聽。最後的處置是日本軍部的政策,於各街庄(鎮、鄉)將廟宇改成一個臨時的收容所,至最後階段,將所有的指導份子監禁起來。」
「什麼是指導份子?」
「像街庄長、大地主、地方有力者最重要的就是政府的黑名單人物。」
「這地方的黑名單人物是誰?」
「第一名是吳三連,第二名是莊真(莊垂勝),第三名就是你了。但是這份黑名單昨日已經燒掉了。」
「可是這怎麼要燒掉呢?這不是國民政府的功臣榜?」雖然這樣輕鬆的說著,吳新榮嚇出一身冷汗。
他曾聽台北的朋友說,日本特務手上有一份黑名單,若美軍攻台,就要把他們統統抓起來殺了,以避免和美軍裡應外合。幸好最後沒有發生,否則自己會命喪何處都不知道,更可怕的是,這簡直是台灣精英的大屠殺。
他定了定神,問道:「你想日本將來要向那裡去?」
「日本人最聽天皇的話,所以這次的投降,以天皇的命令一定不發生問題。但是日本已經屬無產國家了,即使有一句『天皇共產制』的話,我想這也許最適合日本的現況,我歸國後也向這條路走。」平柳默然的說。
吳新榮要得到的答案已經有了。他其實最想知道的是,在台灣的日本人會不會不甘心戰敗,最後負隅頑抗。顯然,日本人「最聽天皇的話」,應該就是放棄對台灣的統治,準備回日本了。至於日本未來如何走,已經不是他關心的課題。他更關心的是:台灣未來要如何重新開始。
吳新榮的憂心不是沒有道理的。最不甘心離開台灣的,是來台灣殖民的日本政府官僚,特別是長期居留,已經習慣了台灣生活的日本人。
他們在台灣有特權,有房子,有財產,有各種優渥的生活條件,高人一等的社會地位,有各種人脈關係,一旦離開,財產全部歸零,回到日本,他們將一無所有,成為徹底的「無產階級」。更何況戰敗的日本,也是徹底的貧困了。
他們當然不甘心,要做最後的一搏,即使只是渺茫的希望也好。
台灣人之中也有殖民體制的既得利益者,如辜顯榮家(辜顯榮已過世,由辜振甫主持家族事業),以及一些御用紳士如許丙、板橋林家的林熊祥等,他們不甘心失去既得利益,於是和日本軍部的少壯派軍人結合起來,計劃號召更多士紳組成「台灣政府」。
這等於是違抗了天皇的命令。但少壯軍人認為台灣有十七萬軍人,還有五十幾萬日本人,結合台灣地方士紳地主,加上台灣人順從的本性,早已習慣殖民體制,未始沒有機會一搏。這個會議,後來被稱為「草山會議」。在計劃中,他們打算請霧峰林家的林獻堂擔任獨立政府的委員長,板橋林家的林熊祥擔任副委員長,辜振甫任總務長,許丙為顧問。
8月19日,許丙和藍國城去拜訪林獻堂,但不知道為什麼,並未提出獨立政府的計劃,只是邀請他去台北一起求見總督。
8月22日,辜振甫、林熊祥、許丙等人利用與杜聰明、林呈祿等人一起去見總督安藤利吉的機會,說明了獨立的意向。安藤當場感到不安了。這是違抗天皇的命令。同時不歸還給中國而獨立,只能說是日本在背後操控,和戰勝的盟軍為敵,不必想也知道機會渺茫,更違反了日本投降的國際公約。
過兩天(24日),安藤利吉就運用《台灣新報》公開表明:「以最近本島有力人士的來訪為契機,安藤總督對於時局的急遽變化與本島之今後,簡明率直地揭示其方針……,特別勸戒島民切勿輕舉妄動,並明白表示絕不容許獨立運動或自治運動。」
若不是安藤總督全力阻止,台灣無法交由盟軍與中國政府接收,說不定會重開戰端也不一定。而這正是少壯軍人所期望,卻是台灣人最不樂見的。
洶湧的暗潮不只是獨立運動。
8月22日左右,一個叫秋水大尉的日本軍官來到陳逸松事務所,他是知識份子從軍,所以明白,要做事得找有影響力的人。他直接表明:台灣是日本殖民地,許多日本人來到台灣,現在有近五十萬居民,他們都很愛台灣,把台灣當做是自己的故鄉,而今日本戰敗,能否向中國政府租借台灣,租期五十年,租金每年三百萬元。你看這樣行得通嗎?」
陳逸松當場就拒絕了。那日本軍官不死心繼續說:「可是我們日本人真的很喜歡台灣,要是台灣人同意,我們再向國際間辦交涉。」
陳逸松拒絕道:「這個我第一個就不同意,怎麼去說?」
這個軍官想利用台灣人為主體,去辦國際上的交涉,那就與日本不放棄台灣,意義上是不同的。
無論獨立運動與租借,都可以反映出在這無政府的時刻,在政權輪換的巨變下,台灣是如何的不穩定。
政治上層如此,那民間呢?
日本的中下層公務員、教師,已經開始打包,他們帶不走的,太重的東西,如家俱、鋼琴、樂器、書籍等,以便宜價格出售。由於廈門街一帶是日本公務員所居住的地方,日本人把舊物擺在街道邊出售,也有人來收集,慢慢形成了市集,後來這裡竟成為舊書與舊貨的商場。至今,廈門街仍是舊傢俱的賣場,旁邊的牯嶺街有一度是台灣最大的舊書市集,後來雖然因為政策將舊書遷到光華商場,但還是有老店不走。如今書市不景氣,但二手書並未沒落,牯嶺街依然有不少家舊書店。這都是1945年鉅變帶來的遺留風貌。
(7之1)